从“社会训诫”走向“隐喻”,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摄影在语言上的本质性变化。1996 年,庄辉开始了
大合影系列第一张作品《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新安县北冶乡社火队合影纪念》的创作,既是对集
体的戏谑与消解,也是对自我作者身份的反思。1997 年,洪磊执导创作了《紫禁城的秋天》,他将一只死鸟
放置在故宫的石台阶上,一种不祥的波诡云谲的隐喻扑面而来,后成为其代表作。
在命名上,经历了新摄影、观念摄影、当代摄影的中国摄影也还在寻求其合适的命名方式,本文在此使用的“执
导型摄影”概念也是出于试图摆脱某一个特定用语导致的时间区间而选择的临时用法,它是来自于西方艺术批
评词汇的变体,比如艺术批评家 A·D·柯曼(A. D. Coleman)早在 1976 年就开始使用“导演模式”(the
directorial mode)来表述艺术创作,这也是从电影的制作方式衍生而来。
从艺术体制的角度去探究,我们会发现,由民营资本助推的美术馆在中国的兴起也带动了执导型摄影的发展。
在创作层面,进入 2000 年,更多的艺术家开始了执导型的摄影实践,在诸多的实践中,所使用的话语资源多
来自于寓言、传说、地方剧目、民间文化,比如韩磊的《赤沙镇》系列(2005 年),借用陕西关中偏僻地区
赤沙镇关于十三种惩罚恶人的民间风俗中神秘而暴力的化妆术进行记录,并进一步演绎,以迎合他“对摄影术
里早期照片的理解”。
与此相对应的景观是,另一些艺术家站在全球化的视野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和文化议题。2000 年,杨福东创作
了《第一个知识分子》,题目里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分明是在隐喻着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这也是艺
术家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未知所做的表达:衣衫破烂有如遭人殴打的男子(知识分子)站在背后耸立着摩天大
楼的都市马路上,手提砖头,却不知道砸向谁,这攻击对象的缺失,也隐喻着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全球化语境
下的知识分子的不确定的未来和困境。
摄影与行为艺术的互动在 2000 年后也变得普遍,与世纪之交的很多摄影形态不同的是,年轻一代开始反观图
像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将讨论的焦点放置在恋像癖、图像与传播、图像与消费以及考现学等议题之中。
2004 年,鸟头小组在上海成立,成员有宋涛和季炜煜,他们的创作以摄影为基础而不受其所限。从早期的《新
村》开始,他们的镜头捕捉任何能涉及的事物,将关于他们自身的成长思考逐渐内化到他们的图像语境中。在《新
村》和《千秋光》等作品里,他们都使用了朋友作为演员去进入艺术家的记忆地理之中,经历或缅怀。在不同
的阶段呈现多个自我更新进化的“鸟头世界”。在其最新作品《鵟》中,他们将自己的组合名称进行意象发挥,
展现他们对于图像的野心与处理能力。
在图像传播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文化符号的抗争史,而符号意义正是通过视觉的重演和传播的重复得以
确立,图像扮演了文化符号合法性的助产士,“可以肯定的是,影像产生符号”(德勒兹)。在这里,图像同
时也变成了富有阶级和身份区隔的精英眼神—衣衫破烂者被定义为受审的文化符号和图像逻辑。
2009 年,蔡东东完成作品《腊月初八》,是对西班牙艺术家戈雅作品《1803 年 5 月 3 日:枪杀马德里保卫
者》的戏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对象呢?在这个作品里,他利用了拍摄和射击在词源学上的同构,它们都归
于“shoot”一词,相机处的位置就是枪支的位置,我们如今处于图像的汪洋大海,没有岛屿,依赖图像,并
借助于图像对他人做出审判。
陈维的《陶醉史》是一组考现学的情景剧,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通过搭建实体舞台、布光、烟雾、运用色彩
排演一场大汗淋漓,荷尔蒙与迷醉气息交织的青年午夜场叙事剧情。在这组作品里,陈维既展示了迷醉,同时
也展示了迷醉的消失。
在执导型摄影变得尤为普遍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开始尝试利用混合媒介和现成品图像进行更为自由和精准的图像合成
实验,在他们的实践中,材料的属性和合成的过程本身所体现的机制就在表征意义的生成。2013 年,张巍凭借作品《人
工剧团》获得色影无忌第四届年度新锐摄影师大奖,后引发争议。《人工剧团》以普通人的身体构造为基础,是经由
作者 ps 拼贴而成的明星肖像,它演绎的是当下的“生产—消费—生产”模式的内在逻辑隐喻,尤其是关于身份的
生产与消费循环。在其 2020 年新作《人偶档案》里,他通过重新编码复原来自网络搜索的历史文献、电影截图、古代
绘画、经典纪实摄影等素材。以玩偶团体的样式来模拟人、事件和行为,篡改原有的现实模型并摧毁其视觉结构和历
史逻辑的“合理性”。
而任何一种摄影形态的命名,必然会本着趣新原则,因而也必然面临簇拥进而被消费和滥用的态势,在大量的执导型、
拼贴、挪用、合成等创作进路的背后,问题意识便成了甄别同行者的重要法则,它的有无,关系到此类摄影形态是否
还有其价值。因而,在成功学和投机心理普遍盛行于摄影生态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这一看起来很“当代”的
面孔。
分层:档案热、民间影像与图像写作
2018 年的集美·阿尔勒发现奖颁发给了以动画作为创作主体媒介的艺术家雷磊及其展览《周末》,是因为他的展览《周
末》触及了图像这一议题。借此,董冰峰提出问题:艺术作品(art works)重要,还是艺术文献(art archive)重要?
图片(picture)重要,还是关于图片生产的制度及其观看方式与立场重要?这一问题的提出,某种程度上也在回应越
来越多的以图像现成品(包括图像档案)为主要创作资源的艺术家的实践。
就“使用”图像的方式来说,其历史不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要回到历史的线路,向档案或文献求取资源?在
连州摄影博物馆夏季展期间,策展人董冰峰在私下交流中做了简单概括,即福柯 的反治理,阿甘本 的生命政治,阿比·瓦
尔堡 的图像蒙太奇。关于档案热的话语实践,我们从阿比 - 瓦尔堡的“图像蒙太奇”里看到了一种基于作者的集权,
一种德里达 所说的“档案病”。
档案热(archive fever)变成了急迫的思想资源,艺术家们依赖于此为自己的创作开设处方,因为德里达和埃里克·普
雷诺维茨(Eric Prenowitz)在《档案热》 (1995)里,曾经回应道,“对档案的处理不是一个关于如何应对过去的概念。
它是一个抛向未来的问题,一个关于未来自身的问题,一个对明天反馈、承诺和担负责任的问题。只有在未来我们能
找到关于档案的真正含义。也许,不是明天,而是更远的将来,或者永远不能到达的将来。” 从《档案热》的话语里,
我们能觉察出一种“反治理”的路径,一种通过对过去及当下的重写而以独立自主的面貌进入未来的构想—未来档案。
在国内的艺术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关于图像使用的面向,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前文所说的“档案”图像的使用,
是对历史的审定与重写,并深入其中探究其运行逻辑与权力关系,以及与当下的上下文联系和反思,第二,对于家庭
相册与个人史的展示和使用,即民间影像的再激活;而在更为年轻的艺术家那里,各种档案图像和民间影像,被打乱
组合,自由地穿梭于图像、档案、文本、声音、装置,甚至于包括绘画之间。进入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图像写作实验中。
因此,本章节以“使用图像”来描述以上创作实践,而没有采用“档案”作为定语,就是想说明,档案只是使用图像
艺术现象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艺术家张大力在《第二历史》里调取各种历史图像,以对比研究的方式对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被权力操纵的图像如何
被篡改,以及权力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机制予以展示。在上海艺术家组合鸟头那里,这种对于图像的“使用”已经进行
了 8 年有余,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是自己拍摄的图像,并且不满足于这些图像本身所携带的意义,将其改造成图像装置,
所以展览中呈现出的作品,既有对摄影的过多装裱所带来的调戏,又有因他们使用图像的叠加与涂绘以及镶嵌进各种
玩具所开发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剧场。
艺术家孙彦初近几年执迷于对民间那些飘零的图像进行改造,既有将图像的意义借用,并进行延展的行为,也有通过
倒置、涂绘、剪裁、连线等方式对图像原有意义进行的抵制行为。这是他对图像本身属性的思考和撕裂。比如在《虚
构集》里,基于对图像不断阅读的过程,加之小时候受给邻里乡亲画画的父亲的影响,孙彦初开始启动绘画这一媒介,
通过“篡改”和“涂抹”的动作,在图像上,诋毁原有图像已经固化的意义,利用媒体上读到的乡村凶杀故事,以及
所使用的图像的时代烙印,在图像上,经过覆盖、嫁接和调侃,从而修筑新的情节,以强化另一种看起来更加成立,
并且显得强大的图像叙事逻辑,但从他保留的依稀的原图像残留物中可以看到这两种叙事所争夺的中间地带。
以上两种近乎图像体操般的拓扑学实践在蔡东东那里,有着更加举重若轻的体现。他从淘宝上批量收购的民间照片(包
括底片和照片现成品),进行折叠、卷曲、揉搓、镂空、打磨、编织、灼烧,并且加入相应的装置(相机、镜面、水
龙头、石头),将这些本已显得平淡的照片从时间赋予的历史影像中挽救出来,经过处理的图像装置开始自己揭示图
像的多义与骗局,消解了历史影像庄严的神圣感,也将飘零的跨越几十年历史的个人纪念照集合成时代和记忆的群像
进行社会政治语境上的对比。
这些艺术家的“使用”行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利用原有图像的最初语义来进行发挥,这个发挥里有放大,也有抵制,
有援引,也有篡改。他们不再沉迷于现实,而是通过对一些有现实场景的图像的使用,使得使用方法所展示的步骤与
路径,揭示图像与大众、图像与历史、图像与政治、图像与媒介之间的运作逻辑和关系。
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曾经是摄影创作坚定的拥护者,但面对新的媒介和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转向图像的“使用”。对
于图像在历史、记忆、图像背后的操控机制等方面的重写,基于图像作为引擎的各种语义的游戏、篡改和排布,从而
大大延展了以摄影作为出发点的艺术家们的创作视野和方法论。
似乎是,那种作为专职“摄影人”的身份优越感在衰减,不是说摄影这个媒介式微了,而是指摄影所面临的语境和媒
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因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图像的生产制度,还是观看方式,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赖快门的单一车间生产
方式,正在向轰轰烈烈的社交媒体图像分发交棒。这一切拜移动互联网所赐。作为图像生产者的被追捧的作者变成了
社交媒体不断劳作的网民,图像不再是凝视的主要对象,而是作为自我肉身的代言人,进入社交网络进行交流,图像
作为隔空传送和分发的身份标识和资源,甚至图像变成了权力,每个人都在疲于奔命地展示自己,争夺这种权力。
这种转向,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层面也向我们释放出一个信息,即艺术家们不再困守一个渠道,而是跨越媒介,艺术家
们已经开始频繁尝试一种叫做“图像写作”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在操作层面,也是将图像作为资源,而不是凝视的
本体。
在今天,宣布自己是摄影师,或许不如宣布自己是一个使用图像的艺术家来得有效,而后者更容易准确地进入图像在
今天的问题核心。如果说图像作为现成品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在面向过去时的话,那么我们从一些艺术家的实践中,
能够看到他们基于档案图像和民间影像的转译,对于当下的思考与行动,当然档案不能囊括全部图像,它甚至某一刻
会变成德里达所说的“幽灵文学”,但将档案变成批评方法,会有力的进入当下境遇。因而,不是所有的图像都具有
历史的属性,它更多的也是吸引艺术家们面向未来做出思考。
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两种尴尬处境:一种是历史或档案(包括图像现成品)成为方法论,并晋升为艺术时尚,趋之若鹜;
而另一种则是,既然涉及了重述,那么,我们重述的行为也或许和我们面对的历史一样,成为未来的重述对象。
鸟头
成立于 2004 年,
由宋涛(b.1979)和季炜煜(b.1980)组成。
工作和生活于上海。
“鸟头”源自一次为文件命名而来的随意键盘敲击。鸟头以摄影
为创作基础而不被摄影所框限。他们的镜头捕捉任何能涉及的事
物,将关于他们自身的成长思考逐渐内化到他们的图像语境中。
他们结合照片矩阵,拼贴,装裱,装置,摄影书写各种对于照片
的使用方式,在不同的展览空间和环境中呈现多个自我更新进化
的“鸟头世界”。
重要展览
激浪之城:世纪之交的艺术与上海,UCCA Edge,上海(2021)
海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20);
生活城市 , 泰特现代美术馆 , 伦敦(2017);
第七届深港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 , 深圳(2017);
第六届莫斯科双年展 , 莫斯科 , 俄罗斯(2015);
2013 年被首届 HUGO BOSS 亚洲艺术大奖提名入围;
2012 新摄影,MoMA,纽约,美国(2012);
重新发电 -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
(2012);
光国,第 54 届威尼斯双年展 主题展,威尼斯,意大利(2011);
2011 艺术家档案 东京国家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年展,国家艺术中
心,东京,日本(2011);
中国发电站 - 第二站,ASTRUPFEARNLEY 现代美术馆,奥斯陆,
挪威(2007)。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泰特现代美术馆,英国伦敦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美国
瑞士尤伦斯基金会,瑞士
Wemhoner 收藏,德国
Alexander.tutsek.stiftung,德国
THE MARGULIES COLLECTION,迈阿密,美国
ASTRUP FEARNLEY 现代美术馆,奥斯陆,挪威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
坪山美术馆,深圳,中国
江南布衣,杭州,中国
相片不再是相片,而是成了创作的某种素材。这个基调似乎从鸟
头的创作初期就定下了。一开始就不信单张照片的意义、不信“决
定性瞬间”。如同生活本身,不是由片刻瞬间组成,而是连续不
断的每分每秒,像流淌的河流一般无法切断。相片像场“生活流”。
从有着上下语境的相册到上百张相片组成的“照片墙”,那些经
由他们手拍出的一张张相片成为了某种意义的元素,它们重新编
码得来了新的图景、新的意义。而后是对相片的装饰,像是一场
戏仿游戏。鸟头把相片如同古董画作一般进行隆重的装裱 : 柚木、
鳄鱼皮、漆器工艺、传统湿裱、纹样绢包裹……这一系列的“隆
重”改变了相片的“质地”,让其煞有急事地成为了“装置”。
还有书法。在相片上书写,由此相片转变成了“背景”,让出了“视
觉主体”的位置。然后是更加激烈的涂抹、撕裂、钉子、粘合剂、
玻璃胶……各种色彩、痕迹、质地。各种玩法在不断试验中越来
越顺滑,已褪去了初期的生涩。相片被嵌入了不同的语境:有时
是疏朗淡雅的北宋,有时是躁动铿锵的朋克金属,有时是无邪的
涂鸦……
鵟,是鸟,指老鹰,读音是“狂”,一个音形意都非常贴合鸟头
的汉字。《鵟》是纪念鸟头的创作呈现,这些作品出现在 2019
年鸟头于中国连州的个展上。这些新作有豁然开朗的意味 : 在对
相片“装置化”的道路上,鸟头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52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253
8262
鸟头 鵟 -007
榆木 黑白照片 彩色照片 丙烯颜料 中国墨 印章 码钉 银锔磁钉
树脂 独版 签名 证书 2019
小:16.3×16.3cm.;大:30.5×36.5cm.
RMB: 40,000-60,000
BIRDHEAD CRAZYBIRD-007
Elm wood, black white photo, color photo, acrylic color material,
Chinese ink, seal, code nail, silver curium magnetic nail, resin,
Exclusive Version,Signed ,Certificate
8262
王宁德创作《有形之光》的方法避开了将图像固定到纸质媒介表
面上的化学过程,转而将一张完整的图像在透明胶片上有组织的
进行碎片化,当暴露于特定的照明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幅完整
影子的图像。最终的结果是,艺术家直接用光绘画,通过电脑和
人手的劳作过程创造出幽灵般的图像。王宁德通过这一系列影像
装置作品来审视摄影过程的本质和奥秘。《有形之光》系列里的
作品所呈现的效果更接近于老式的照相暗盒
—一个仿佛悬浮在
现实本身之上的幻影。此外,这些由数百个单位组成的网格图像
颠覆了传统摄影惯常所见的独幅裁剪的作品。在柏拉图的“洞穴
寓言”中,墙上的阴影是囚犯的现实。虽然这个寓言是为了阐释
柏拉图的形式论,但最能引起当代人瞩目的是寓言中对墙上阴影
的集体迷恋的那种预言性描述。王宁德把这些作品形容为有意的
产生“虚幻的感觉”,它们实际上是对摄影作为一个整体的幻觉
力量的洞察。而艺术家所选择的主题:天空、树林和云彩,都以
表现和抽象两种形式表达了这一原则。作为一个系列作品,《有
形之光》系列以独特的视角讨论图像本身的原素,重新定义了墙
上谚语般的阴影带给我们的沉迷感觉。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54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8263
王宁德 有形之光
亚克力 蜂窝铝板 透明灯箱片 2/3 签名 证书 2015
147×107×5cm.
RMB: 80,000-150,000
WANG NINGDE THE VISIBLE LIGHT
Composite Materials, Signed ,Certificate
王宁德
1972 年出生,现工作并生活于北京。
重要展览
2020 《无名》,奥胡斯图像美术馆,奥胡斯 ,丹麦
2019 《负光》,影像上海 ,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 ,中国
2018 《有形之光》,Bryce Wolkowitz 画廊,纽约,美国
2017 《无名》,影像旧金山“艺术家焦点”,福特·梅森会展中心,旧金山,美国
2016 《无名》,影像上海,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中国
2015 《有形之光》,派拉蒙电影制片厂,洛杉矶,美国
2014 《有形之光一》,M97 画廊,上海,中国
《有形之光二》,M97 项目空间,上海,中国
2011 《某一天(1999 - 2009)》, m97 画廊,上海,中国
2010 《王宁德作品展》,巴黎 - 北京画廊,巴黎,法国
《王宁德作品展》,禅画廊,东京,日本
《要有光》, 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 I、III,北京,中国
2007《王宁德作品展》, SF Camerawork, 旧金山,美国由安迪 . 沃霍尔基金会赞助
2006 《王宁德作品展》, 红庐基金会 , 伦敦,英国
《某一天》, Goedhuis 画廊 , 纽约,美国
《灵魂的疆域之外》, 帝门艺术中心 , 北京,中国
2005 《在历史与梦幻之间》, 鲁迅美术学院 , 沈阳,中国
1999 《走向更昏暗的地方》,广州博尔赫斯书店 , 广州,中国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PILARA 基金会,旧金山
亚历山大·图切克基金会, 慕尼黑
洛杉矶县立美术馆 (LACMA),洛杉矶,美国
白兔收藏,悉尼,澳大利亚
Uli Sigg 收藏,瑞士
红庐基金会收藏,伦敦,英国
Franks-Suss 收藏,伦敦,英国
Agnès b. 艺术基金会,巴黎
法国国家文化部,巴黎
伯格收藏,香港
广东美术馆,广州
重庆美术馆,重庆
湖北美术馆,武汉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
中国丽水摄影博物馆,丽水
255
8263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56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蒋志
1995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1971 出生于湖南沅江
重要展览
2020 《这个我能变好吗?》,刺点画廊,香港,中国
2019 《蒋志个展—震源》,SiloSilo, 苏黎世,瑞士
2018 《蒋志 | 去来》,刺点画廊,香港,中国
《我认出风暴—蒋志》,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2017 《范沧桑 | 蒋志个展》, Hadrien de Montferrand 画廊 , 北京,中国
《我们—蒋志个展》,TKG +,台北
2016 《一切—蒋志个展》, 深圳 OCAT,深圳
《注定—蒋志个展》,魔金石空间,北京
《蒋志:一半》,Jewelvary,上海,中国
2015 《蒋志:一现》, 白立方,香港,中国
2012 《窄门》,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
《情书》,M97 画廊,上海,中国
《不纯之光》,Saamlung 画廊,香港,中国
《如果这是一个人》,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
2011 《一念,沪申画廊》,上海,中国
2010 《表态 3—蒋志的一个展览》,站台中国,北京,中国
《蒋志个展:神经末梢的温度》,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曼谷,泰国
《蒋志个展:颤抖》,玛吉画廊,马德里,西班牙
2009 《表态 2—蒋志的一个展览》,奥沙艺术空间,香港,中国
《表态 1—蒋志的一个展览》,奥沙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2008 《蒋志个展:白色之上》,奥沙艺术空间,香港,中国
《蒋志个展:神经质及其呓语》,玛蕊乐画廊,北京,中国
《蒋志个展:照耀我》,DF2,洛杉矶,美国
2007 《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得简单》,M97 画廊,上海,中国
2006 《蒋志个展:双人房—03 房》,朱屺瞻艺术馆,上海,中国
1999 《“木木”蒋志摄影展》,博尔赫斯书店,广州,中国
重要奖项
2012 “瑞信·今日艺术奖”
2010 改造历史(2000 - 2009 年中国新艺术)学术大奖
2009 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
2002 香港国际电影短片节“亚洲新势力—评委会大奖”
2000 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BSI 艺术收藏
DSL 收藏
广东美术馆
时代美术馆
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
美国胡德艺术博物馆
Kadist 艺术基金会
澳大利亚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香港 M+ 博物馆
希克收藏
257
8264
蒋志 旧颜 07
收藏级艺术微喷 3/6 签名 证书 2016-2017
99×132cm.
RMB: 50,000-80,000
JIANG ZHI OLD FACE 07
Ultragicleetm on Fine Art Paper,3/6,Signed, Certificate
8264
上色不均的水泥墙面、永不枯萎的塑料假花、玻璃板下压着的老
花布或者略带洋气的蕾丝边、木框窗户上的磨砂玻璃纸……这些
画面中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细节,均来源于蒋志对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记忆。蒋志的《情书》明艳清透又感伤凄绝,花是信使,
从此间渡往彼岸,火焰是临行的喃喃私语。《旧颜》则尽是尘封
往事的味道,经历过 70-80 年代的人,记忆中都有这么一盆假花,
一个斗柜,一处窗台,一张梳妆台……蒋志成为潜入了每个人记
忆的灵魂布景师,复原了旧时光被封印的精致假象,仅存的破绽,
来自那不属于日常生活的美丽。
258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孙彦初
1978 生于河南周口,现工作和生活在郑州
重要展览
2019 无镜之景,谢画廊,中国长沙
显影绘和虚构集的节选,M97 今日亚洲 X 孙彦初,法国巴黎
显影绘,东景缘画廊,中国北京
2018 虚构集,2018 亚洲摄影项目,爱丽舍摄影博物馆,瑞士洛桑
2017 虚构集,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中国连州
虚构集,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中国厦门
显影绘,M97 画廊,中国上海
2016 “暗房里的自大者”,香港巴塞尔,中国香港
2014 沉溺,北京现在画廊,中国北京
2013 迷途,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中国连州
2011 沉迷,西五艺术中心,中国北京
重要奖项
2017
集美·阿尔勒发现奖提名,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中国厦门
2016
第四届中国摄影排行榜,丽水摄影博物馆,中国丽水
2015
谷仓摄影样书 马丁.帕尔评审奖大奖,连州国际摄影节,中国连州
2012
第四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最佳摄影师大奖,中国济南
2011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2011 年度新摄影奖,中国连州
2010
MIO 摄影奖评审员(森村泰昌)特别奖,日本大阪
勒瓦鲁瓦—爱普生摄影特别推荐奖,法国勒瓦鲁瓦
259
8265
孙彦初 雪松
明胶卤化银 独版 签名 证书 2019
50.7×61cm.
RMB: 25,000-40,000
SUN YANCHU CEDAR
Gelatin Silver Halide, Exclusive Version, Signed, Certificate
8265
在“显影绘”系列作品中,艺术家以摄影媒介为原料创作了他的
化学绘画和暗房冲印。孙彦初的摄影植根于传统摄影,创作方式
实际上不是用镜头和相机拍摄,而是用化学、相纸和画笔作为摄
影创作。在经过此种技术的几次实验后,孙彦初用经验和直觉来
控制化学药水、温度、光照和显影过程,从而展现出他的显影绘
作品中独特的效果。他说,这种创作的过程和显影后的结果—
黑墨的层次和颜色的渐变效果—非常像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
法,艺术家从小就接触到这些。孙彦初的“显影绘”作品融合了
他对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摄影创造的热情,诞生出一种全新
的语境和美学感受,一次绝无仅有的崭新体验。
260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蔡东东
1978 出生于甘肃天水
2002 就学于北京电影学院,目前生活工作于北京 / 柏林
重要展览
2019 中国上海 狮语画廊 《造相术》
2017 美国纽约 Eli KLEIM 画廊 《照片的专制》
2016 美国纽约 Eli KLEIM 画廊 《泉》
美国康州 康涅格学院图书馆《脱靶》
台湾台北 百艺画廊 《让之在》
2015 中国北京 三影堂 +3 画廊 《再生式》
中国北京 Tong Gallary 《落石》
中国北京 家里画廊《记忆的移植与切片》
2013 中国上海 五五画廊 《图像 母体 生产 权力》
2012 德国斯图加特 彤德画廊 《制图术》
中国北京 泰康空间 日光亭项目 《向左拉动》
2011 意大利 UNIDEE 艺术基金会 《茶园》
2010 中国北京 泰康空间 《蔡东东》(51 平米第 6 号)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德国柏林 德国国家摄影博物馆
德国埃森 弗柯望美术馆 Museum Folkwang, Essen
德国柏林 德中文化交流基金会
澳大利亚 悉尼白兔美术馆
俄罗斯莫斯科 MAMO 美术馆
意大利 都灵 UNIDEE 基金会
中国广州 广东美术馆
中国北京 泰康空间
中国北京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中国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以色列 尧山艺术基金会
“基于老照片的再创作”一直是艺术家蔡东东的主要手法。蔡东
东将自己收藏的 60 万张老照片作为材料进行创作,通过卷卷曲、
打磨、移植、刮擦、撕扯、灼烧照片,或以装置、雕塑等形式出
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方式凸显了图像对于人的凝视与侵占,等于
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旋转关系。艺术家退出了图像生产者的行列,
站到观众这一边,思考着接受的荒谬和疑难,进而针对已经存在
于现实中的图像开始工作,“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样,对这些既存
的照片做起了手术”。它们部分地来自他过去拍下的胶片,更多
地来自旧货市场,以及宣传部门淘汰的图像资料,他从那里搜集
到各种各样的旧照片和底片,将它们带回“暗房”,不时地琢磨
可行的手术方案 ; 卷曲、打磨、移植、刮擦、撕扯、灼烧等等,
这些手法俨然具有手术刀式的暴力感,但目的在于挽救:发现僵
化的图像背后的某种“戏剧性结构”,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
而这要取决于在他和图像相互审视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增设一
个“刺点”的可能。
261
8266
蔡东东 打靶归来
明胶卤化银 LED 灯箱 5/5 签名 证书 2018
45.5×45.5×174cm.
RMB: 40,000-60,000
CAI DONGDONG B A C K F R O M
TARGET PRACTICE
Gelatin Silver Halide,LED Light Box,5/5,Signed,
Certificate
8266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62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陈维
1980 年出生于浙江,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重要展览
2021 Good Night,昊美术馆,上海
2019 陈维:夜瀑布,大田画廊,新加坡
陈维 : Goodbye,香格纳,上海
陈维:浮沉 & 正午俱乐部,个展及新书发布,Büro, 巴
塞尔,瑞士
2018 陈维 : 你今晚去边,chi K11 艺术空间,广州
陈维 : 落光,Rüdiger Schottle 画廊,慕尼黑,德国
陈维 : 新露,大田画廊,新加坡
2017 陈维,香格纳北京,北京
俱乐部,当代摄影中心 (CCP),墨尔本,澳大利亚
2016 午间俱乐部,JNBY 艺术空间,杭州
2015 午间失眠者,大田画廊,新加坡
在浪里,chi K11 美术馆,上海
昨日商店,Rüdiger Schottle 画廊,慕尼黑,德国
无序之言,Stieglitz19,安特卫普,比利时
夜巴黎,大田画廊,东京,日本
2014 士林巴颂,Ben Brown Fine Arts,伦敦,英国
陈维,安全口画廊,香港
夜空星星无数,澳大利亚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悉尼,澳
大利亚
2012 局部有雨,Rüdiger Schottle 画廊,慕尼黑,德国
More,Leo Xu Projects,上海
2011 预言家的游戏,Glance 画廊,都林,意大利
「花瓶掉了下来,碎了一地。」,SHcontemporary 11,
上海展览中心,上海
漠然之索,创造都市中心,横滨,日本
2010 康复之屋,LISTE 15,巴塞尔,瑞士
陈维摄影 2006-2009,Full Art,塞维利亚,西班牙
2009 局部的忧郁,北京艺术实验室,北京
日常 , 布景和道具,安全口画廊,香港
陈维摄影 2007-2009,M97 画廊,上海
2008 寓言家的小径,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北京
影像和装置是艺术家陈维创作的基本形式,艺术家关注两者之间
的关联和作用。对于习惯在工作室搭建舞台并拍摄影像作品的陈
维而言,影像是装置的影像,同样,装置也是影像的装置。陈
维在创作中不断探讨装置和摄影之间的关系,舞台是艺术家寻
找到的答案之一。装置为艺术家提供源自我的表达出口,而摄
影则提供了更精确的信息面。阶梯、昏黄的灯光、被包裹的物
体,平常的形态和物件在舞台中被重置。艺术家有意使叙事的部
分离场,缺失构成了叙事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光影与空间,人
与城市,通过建构光源,艺术家把抽象的“公共领域”(德语
Offentlichkeit, JurgenHabermas, 1962/1989)转换成一个可被
感知的实体空间。正如古希腊城邦(polis)的市民在广场(agora)
实践公共生活,在光影斑驳的展厅空间中,观众得以分享一种即
兴与诗意的亲近性。
重要奖项
2011 亚太摄影奖
提名
2015 英国保诚当代艺术奖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ALEXANDER TUTSEK-STIFTUNG 艺术基金会,慕尼黑,德国
新加坡美术馆,新加坡
Sammlung Goetz,慕尼黑,德国
乌利·希克收藏,瑞士
chi K11 美术馆,香港
Carmignac 基金会,伊埃雷,法国
UBS 收藏,瑞士
余德耀基金会,雅加达,印尼
DSL 收藏,北京
卢贝尔家族收藏,迈阿密,美国
金泽 21 世纪美术馆,石川县金泽市,日本
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
M+ 收藏,香港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美国
263
8267
陈维 被包裹的雕像
收藏级喷墨打印 裱于铝塑板 5/6 签名 证书 2015
187.5×150cm.
RMB: 80,000-150,000
CHEN WEI WRAPPED STATUES
Ultragicleetm on Fine Art Paper, 5/6, Signed, Certificate
8267
2020 年伊始,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胡为一由此开始思考病患、死亡等话题,
并着手收集各种病患的 X 光片,包括胸片和其他部位。这些片子既有来自
于他个人的,也有来自于家中长辈、素不相识者和一般逝者的。X 光片属于
胶片,材质和数码底片类似,艺术家通过蓝晒法将其显影,很好地消解了
X 光片里自带的黑色,画面因此变得明快起来,同时又伴随哀伤。之后,艺
术家拍摄了许多花朵的图像,将其与 X 光片进行有机结合,为作品构建了
一种生与死的双重维度。对胡为一而言,艾略特诗集中的两则片段,可与
他的创作形成某种开放的互文性。《蓝色骨头》中,X 光片追求的是理性与
客观存在,暗房显影却追求一种主观化的效果。这种彼此相悖的,且无法
通过数码输出去呈现的关系,构成了作品中无法替代的图像生产特性。在
此基础上,艺术家进一步思考所谓摄影真实性的问题:纯客观的 X 光片是
绝对真实的,摄影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与真实相关,可它们都不是真相。
真相并不会因为反映客观和刻画真实而得以浮出水面,相反它躲在 X 光机
和暗房里,嵌在图像生产的机制之中。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64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胡为一
2016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并取得硕士学位
2013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并取得优秀毕业作品金奖荣誉
1990 出生于上海
重要展览
2021 《悬浮在空中的灰尘曾经是一座房》,浙江美术馆,杭州,中国
2019 《胡为一|窗外无窗》,HdM 画廊,北京,中国
2018 《越界—胡为一》,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上海,中国
2017 《例行公事》,东画廊,上海,中国
2015 《胡为一》,亚洲艺术中心,台北二馆,台北,台湾
《两点之间没有直线》,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悦廊,北京,中国
2014 《我静静地等待光从身体穿过》,M50 Art Space,上海,中国
重要奖项
2015 第九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奖
墙报艺术家二等奖
2014 华宇青年奖评委会全场大奖
2013 中国美术学院本科优秀毕业作品金奖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龙美术馆
K11 艺术基金会
白兔艺术基金会
DSL 收藏
昊美术馆
新世纪艺术基金会
265
8268
胡为一 蓝色骨头 No.44
蓝晒法 独版 签名 证书 2020
88×60cm.
RMB: 20,000-30,000
HU WEIYI BLUE BONES NO.44
Cyanotype,Exclusive Version,Signed, Certificate
8268
266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8269
韩磊 摄影作品一组(12 张)
银盐纸基 2/20 签名 1989-2001
50×60cm.
RMB: 150,000-200,000
HAN LEI PHOTOGRAPHY WORKS (12 PIECES)
Gelatin Silver Print, 2/20,Signed
韩磊
1967 出生于河南开封
1989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
现工作、生活于河南省郑州市
重要展览
2018 韩磊:飞来峰, 连州摄影博物馆,连州,中国
2016 虚线:星空间,北京,中国
2016 时差: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南京,中国
2014 Spiral : 韩磊个展 , M97 画廊 , 上海,中国
2012 勿妄我: 韩磊个展 , M97 画廊 , 上海,中国
2010 照相法: 韩磊 + 摄影 , 玛吉画廊 , 马德里,西班牙
2010 间隔: 韩磊摄影展 , 泰康空间 , 北京,中国
2009 照相法: 韩磊 + 摄影 ,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 北京,中国
2008 沼泽:韩磊个展,西五画廊,北京,中国
2007 影像复兴:韩磊摄影展,J Chen 画廊,台湾,中国
韩磊摄影展,汉雅轩,香港,中国
2006 Where is China? 韩磊摄影展,现在画廊,北京,中国
PAGODA: 韩磊摄影展,LOFT 画廊,巴黎,法国
2005 肖像:韩磊,Polaris 画廊,巴黎,法国
韩磊:拍摄于 2005,百年印象画廊,北京,中国
1996-1997
疏离:韩磊摄影展(艺术文件仓库主办)北京 - 柏林 - 赫尔辛基,中国 - 德国 - 芬兰
博物馆与公共收藏
琼斯母亲国际文献摄影基金会,美国 (Mother Jones International Fund for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USA)
埃斯特拉收藏,纽约,美国 (Estella Collection, New York,USA)
法国文化部( French Ministry of Culture)
白兔美术馆,澳大利亚 (White Rabbit Gallery,Australia)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中国 (Three Shadows Photography Art Centre, P.R.China)
泰康收藏,中国 (Taikang Collection, China))
橡子园基金会,纽约,美国( Acorn Foundation, New York, USA)
M+ 博物馆,香港 (M+,Hong Kong)
267
8269
韩磊在 1980、1990 年代间拍摄过一批黑白照片,视角围绕着故乡开封一带的日常生活及其旅行展开,看似细微,却堪称留住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事实上,
罕有比它们更打动我的摄影了,如果说数码技术带来的图像景观日渐成为摇散我们心神的海市蜃楼,那么,他的这些作品则像一口朴实、幽深的井,让我们
得以再次凝视自己,窥探到记忆底部的根和天空。他拍摄的那些人物、面孔和环境,表明了集体性的断裂状态:失去了传统的文化根基,又对现代性充满了
渴望、迷惑和误解,其中的静滞感溯及了几千年不变的、令人窒息的某种盲目,而动态的捕捉几乎预示了此后的都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一
种畸形的庸俗主宰了整个现实表情。就布勒松所言的“决定性瞬间”而言,韩磊拥有天才般的直觉或嗅觉,甚而可以说,是那些瞬间在等着他。他创造了自
己的语调:疏离而不安,既不沉溺于对于苦难与变迁的文献性纪实,也不走向抒情式的个人审美。疏离,是为了不陷入同等的盲目和庸俗之中,作为主体的
那个自我敏感于所见、所觉察的那一切,但不可能以先知的态度去感召,或者化身英雄去拯救,疏离赋予了自我一个旁观的空间和距离,或许称之为旁观的
缝隙更准确——摄影本该是“秘密的和轻盈的”,但必然牵连着土地、血缘、制度和历史,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宿命,构成个体与集体之间分裂又休戚与共的
悲剧,而他其实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晰。(朱朱《瞬间的解脱》)
268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国当代摄影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8270
王福春 火车上的中国人
银盐纸基 4/30 签名 证书 1998
58×49cm.
RMB: 15,000-20,000
WANG FUCHUN THE CHINESE ON THE TRAIN
Gelatin Silver Print, 4/30,Signed, Certificate
出版:《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摄影作品集》封面,黑龙江美
术出版社,2001 年;
《火车上的中国人》封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 年。
8270
说明:王福春被誉为“中国火车摄影第一人”,北上漠河、南下广州、
西至格尔木、东到上海,行程数千次,他拍下 20 多万张火车上
的中国人的照片。从绿皮火车拍到白皮高铁,他见证了火车上的
人生百态,记录下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摄
影家最重要的代表作。2000 年起,曾在丹麦奥胡斯 IMAGE 形象
艺术摄影展馆、平遥国际摄影节、莫斯科国际摄影展、中法文化
年“平遥在巴黎”、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上海爱普生影艺坊等
展出。画册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师“阿尔卡特”大奖。
限量 4/30,附百年印象画廊证书。
王福春(1943-2021),毕业于中国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
任哈尔滨铁路科研所摄影师、编辑。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
有《火车上的中国人》、《黑土地》、《东北虎》、《中国蒸汽
机车》、《大东北》等摄影专题。其中,2001 年出版发行的《火
车上的中国人》画册获 2002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优秀摄影师
画册阿尔卡特大奖”金奖等多项大奖;2018 年,《火车上的中国人》
进入中国美术馆办展;2019 年,该系列作品又在大英铁路博物馆
亮相,并开启了在英国多家知名博物馆为期 3 年的巡展。
出版资料
269
8271
吴家林 哈尼农舍
银盐纸基 1/30 签名 1988
50.5×40.5cm.
RMB: 15,000-20,000
WU JIALIN HANI COTTAGE
Gelatin Silver Print, 1/30,Signed
出版:《云南山里人:吴家林摄影集》,云南美术出版社,1993 年。
8271
说明:摄影师代表作品之一,背面带版号及签名,品相完好。
1993 年以后,吴家林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国际亮相并引
起世界影像大师的关注。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中,吴家林坚定地
避开潮涌长期深入民间,着眼于普通百姓在自然状态中的美好人
性,坚持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瞬间。马克·吕布称吴家林的作品
为“治疗淫逸无度的城市病的良药”。附带有出版的摄影师签名
画册。
吴家林(1942-),出生于云南昭通。1968 年开
始自学摄影。1981 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原
云南新闻图片社社长,2002 年退休后成为自由
摄影家。1997 年 6 月,《云南山里人》系列作品,
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2003
年,代表作《拉家常·成都1999》。被收入《亨利·卡
迪尔·布列松的选择》影展及画册。2006 年 11
月,《吴家林·中国边陲》作品集,进入世界摄
影大师系列作品丛书(法国著名的摄影“袖珍黑
皮书”)出版。1989-2014 年,其个人摄影展
曾多次在巴黎国际摄影节和美国休斯顿国际摄影
节展出,先后在德国赫尔腾国际摄影节、纽约国
际摄影中心 ICP、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博物馆、
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法布尔艺术博物馆、
巴西艺术博物馆、美国达拉斯 PDNB 画廊以及中
国台湾、香港、北京、上海、平遥、连州、西安、
淮安、杭州等地展出。
出版物资料
270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外名家摄影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ers
8272
肖全 巩俐
银盐纸基 签名 1994
22.5×15cm.
RMB: 15,000-20,000
XIAO QUAN GONG LI
Gelatin Silver Print, Signed
说明:此幅照片出自著名人像摄影师肖全之手,是
为电影《摇啊摇,要到外婆桥》拍摄的电影剧照。
照片品相完好,背面带有肖全的签名与版权印章。
8272
271
8273
肖全 杨丽萍
艺术微喷 签名 1996
51.5×61cm.
RMB: 15,000-20,000
XIAO QUAN YANG LIPING
Ultragicleetm on Fine Art Paper, Signed
说明:此幅照片出自著名人像摄影师肖全之手,拍摄于 1996 年,
年轻的杨丽萍正在表演孔雀舞。最难得是照片带有杨丽萍与肖全
的双签名,是肖全人像摄影收藏中的极品。对于肖全的摄影,杨
丽萍曾经说道:“我是天蝎座,是完美主义者,不太喜欢有人跟
着我拍照,但是惟独对肖全我特别放松,他在我面前拍照我很自
然地接受,我说过,他就是我身边的一棵草,一棵树,或者一朵
云……即便我在暮年的时候,我也很会愿意他来拍我, 他会把我
拍得比较有尊严。”
8273
272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外名家摄影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ers
8274
曼·雷 泪珠
银盐纸基 签名 1932
23.5×30.5cm.
RMB: 15,000-20,000
MAN RAY TEARS
Gelatin Silver Print, Signed
说明:曼·雷代表作 1930 年拍摄的《泪珠》,是一幅梦幻与真
实的超现实作品。作品主人公的眼泪,泪珠,引人注目,令人遐想。
由摄影师基金会 1991 年制作,作品背面有版权信息,品相完好。
8274
曼·雷(Man Ray,1890-1976),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最全
方位的艺术家之一。达达主义的奠基人,先锋摄影大师,诗人,
雕塑家,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创者。
273
8275
曼·雷 情色面纱
银盐纸基 摄影书 签名 1933
30.5×24cm.
RMB: 15,000-20,000
MAN RAY ROTIQUE VOILE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Signed
出版:《MAN RAY》,p37,TASCHEN。
说明:曼·雷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由摄影师基金会 1991 年制作,
作品背面有版权信息,品相完好。
8275
出版资料
274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外名家摄影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ers
8276
劳森伯格 丹吉尔(附摄影书)
银盐纸基 摄影书 签名 1952-1979
作品:32.5×31.5cm.;书:28.5×25cm.
RMB: 30,000-50,000
ROBERT RAUSCHENBERG TANGIER (WITH
PHOTO BOOK)TANGIER (WITH PHOTO BOOK)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Signed
出版:《Robert Rauschenberg Photographs 1949-1962》,
p147,2011 年。
8276
说明:罗伯特·劳森伯格的摄影作品《丹吉尔》(Tangier)拍
摄于 1952 年,收录于《罗伯特·劳森伯格摄影集 1949-1962》
(Robert Rauschenberg Photographs 1949-1962,2011)中。
该摄影集首次收集并调查了劳森伯格对摄影的众多用途,涵盖朋
友们的肖像、工作室照片、融合系列中使用的照片、丝网印刷、
丢失作品和进行中作品的照片——让我们能够根据他对摄影的创
造性使用,想象几乎所有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提供了对劳森伯
格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社会关系的罕见一瞥。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美
国新达达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和波普艺术的创立者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他将绘画和雕塑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
“融合绘画”(Combine Painting),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定义和边界,
创作涵盖绘画、雕塑、摄影、舞台表演和服装设计等多个领域。
275
8277
克里斯托弗·马克斯 安迪·沃霍尔在飞机上(附摄影书)
银盐纸基 摄影书 16/20 签名 1977
作品:18.5×27.5cm.;书:20.5×24.5cm.
RMB: 5,000-8,000
CHRISTOPHER MAKOS ANDY WARHOL ON THE
PLANE (WITH PHOTO BOOK)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16/20,Signed
8278
安迪·沃霍尔自拍像
宝丽来 签名 1980 年代
10.5×8cm.
RMB: 20,000-30,000
ANDY WARHOL'S SELFIE
Polaroid,Signed
8277
8278
说明:克里斯托弗·马克斯(Christopher Makos)的著作《背
景中的沃霍尔·马克斯》(Warhol | Makos in Context)深
入记录了他 1976 年至 1987 年的摄影生活,记录了他在安
迪·沃霍尔身边度过的岁月。书中附 1977 年马克斯拍摄的
沃霍尔照片一张,摄影师于照片正面签署版号和签名,背
面带版权印章,品相完好。
克里斯托弗·马克斯(Christopher Makos,b.1948),纽
约摄影艺术家。在加州长大,后去了巴黎学习建筑学,成
为曼·雷的徒弟并和他一起工作。拍过达利、泰勒、列侬
等名人,最重要的是他记录了属于“中国”的安迪·沃霍尔。
沃霍尔曾说马克斯是“美国最现代的摄影师”。70 年代初
期,他形成了大胆的新闻摄影风格,大量作品在欧洲、美
国和日本的影展、画廊、博物馆展出,被上百家美术馆收藏,
更有数之不尽的报刊杂志见证了这位纽约艺术史上屈指可
数的摄影师的艺术历程。
说明:安迪·沃霍尔通常使用宝丽来相机,因为它快捷、轻松。同时,
他拍摄的大量自拍肖像中,其中一些后来被制成丝网印刷品。沃霍尔的
自拍照,有时是真实的自己,有时是表演,而自拍照是了解他有趣创意
和个人精神的有效途径。作品保存完好,品相较佳,作品背面附印章。
276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外名家摄影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ers
8279
马克·吕布 职工宿舍(附摄影书)
银盐纸基 摄影书 签名 1965
作品:25×35.5cm.;书:26.5×29.5cm.
RMB: 10,000-15,000
MARC RIBOUD STAFF DORMITORY
(WITH PHOTO BOOK)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Signed
8279
说明:马克·吕布的摄影作品《职工宿舍》拍摄于 1952 年的中国长春,收录于《中
国愿景》(Visions of China,1981)一书中。《中国愿景》是从他多次中国之行
中挑选出来的亲密、动人、出人意料的摄影作品。在这些影像中,我们可以发现过
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生活与充满活力的中国梦二者间的所有矛盾力量,这
也是马克·吕布作品力量之所在。摄影书有马克·吕布亲笔签名。
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23-2016),法 国 著 名 摄 影 师, 出 生 于 法 国 里
昂,以来自东方的延伸报道而著称。主要作品有《中国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1966)、《北越面貌》(Face of North Vietnam,1970)、《中
国愿景》(Visions of China,1981)。1957 年发表了报道中国的第一张图片,从
那时起他先后多次访问中国,观察和记录了在中国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
277
8280
安塞尔·亚当斯 冬日的船长峰(附摄影书)
银盐纸基 摄影书 签名 1952
作品:24×18cm.;书:31×39cm.
RMB: 20,000-30,000
ANSEL ADAMS CAPTAIN'S PEAK IN WINTER
(WITH PHOTO BOOK)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Signed
8280
说明:《约塞米蒂和区域曝光》(Yosemite and the Range of Light,
1979)是安塞尔·亚当斯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本书。它既是自然历史,
也是个人历史,它的图像是摄影和保护编年史中的一个里程碑。116 幅图
像中,内容从细节到全景全部囊括在内,内容丰富。有些照片众所周知,
但大多数以前从未发表过。此外,此书是为《时代生活丛书》(Time-Life
Books)订阅者准备的特别版本,带有摄影师签名。《冬日的船长峰》沿
袭了亚当斯作品影调细腻的一贯风格,品相完好。
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1902-1984),著名风光摄影大师,
20 世纪伟大的摄影家、摄影教育家、自然环境保护者,“区域曝光法”
的创始人、f/64 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其风光作品在向人们表达大自然之
美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此外,亚当斯的摄影
理论影响了众多摄影人。
278 影像艺术 Photography
中外名家摄影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Photographers
8281
理查德·阿维顿 肖像三联张(附摄影书)
银盐纸基 摄影书 签名 1960 年代
作品:30.5×65.5cm.;书:30.5×23cm.
RMB: 15,000-20,000
RICHARD AVEDON PORTRAIT TRIPTYCH (WITH
PHOTO BOOK)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Signed
8281
说明:作品《肖像三联张》突破了既有的单人单幅方式,采取了
并置的表现手法,新颖、独特。《理查德 • 阿维顿理肖像》(Richard
Avedon Portraits,1976)摄影书由美国作家、教育家、哲学家
和艺术批评家哈罗德 • 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1906-
1978)撰文,拍摄了玛丽安 • 穆尔,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 • 奥本
海默医生、溫莎公爵夫人、演员玛丽莲 • 梦露等各界人士肖像,
简洁、有力、统一。
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1923-2004),1944 年,
21 岁的阿维顿退役后开始了时装摄影,代表作有《多维玛与大象》
《外套》等。美国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将阿维顿
与布勒松、史泰钦和布兰德并列为“上个世纪职业摄影的典范之
一”。
279
8282
沃夫刚·提尔斯曼 Process (apple tree)
银盐纸基 摄影书 51/100 签名 2012
48×33cm.
RMB: 15,000-20,000
WOLFGANG TILLMANS PROCESS (APPLE TREE)
Gelatin Silver Print, Photo Book,51/100,Signed
8282
说明:正如提尔斯曼作品中对日常主题的一贯关注,Process
(apple tree) 是提尔斯曼对苹果树从发芽、开花、结果过程的影像
记录,由 9 张作品构成。在提尔斯曼的日常关注中,更多呈现而
出的是对自我隐匿趋向。因为被人们视为自然存在的环境,往往
很难深入想到是可以由政治所产生的。作品有摄影家签名。
沃夫冈·提尔斯曼(Wolfgang Tillmans,1968-),出生于德国,
以其广泛的选题和多样的照片尺寸而闻名于世。作品有精妙的创
意过程,包括精心挑选、谨慎排列、整体熟练、控制中心思想等,
进而表达一种始终如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介于公众和私人之间的
边缘地带,并且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提尔曼斯所关注的主题并
非是表面符号化的政治事件,而是并不显眼的日常生活的片段。
又见
—影像艺术专场
RESEE-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y
RESEE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798 艺术区
A04·圣曦中心三层
+86 10 64156669∣www.sungari1995.com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展览中心
20
影像艺术专场
中贸圣佳 2021 上海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2021 SUNGARI AUTUMN AUCTION SHANGHAI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y
上海展览中心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000号
1000 Yan'an Middle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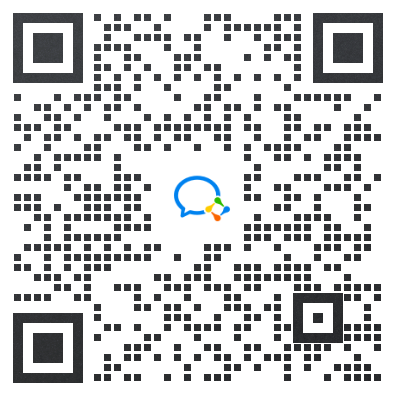


































 该页无缩略图
该页无缩略图



